清明时节雨纷纷,
路上行人欲断魂。
借问酒家何处有?
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——杜牧《清明》
清明时节,细雨连绵,飘飘洒洒地下个不停……
武汉解封,生活重启,却也留下不尽的伤与痛……
截止4月1日,全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81589人,累计死亡3318人。敲下这些数字的时候,我的手在颤抖,心也在哭泣。因为,每一个数字背后,都是如你我一般鲜活的生命,有亲人、有朋友,有思想,更有情感……
刚刚解封后的武汉,殡仪馆门口排起了蜿蜒的长队,市民们前来领取亲人的骨灰。我无法想象他们内心到底承受着怎样的痛苦,有的人撕心裂肺,有的人麻木淡然,将所有的伤痛深埋在心底…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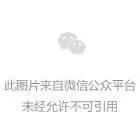
一场艰难的战“疫”走向了尾声,而这场心灵的战役还将持续,可能惊天动地,也可能默默无声。至亲的离去,是我最无法想象、最难以承受的痛苦,这种痛苦,有时甚至会觉得超过了自己的死亡。
在这种痛苦中,人们会不断地回忆亲人的一颦一笑,他说过的每一句话,做过的每一件事,和你一起经历的快乐和幸福,仿佛仍历历在目、恍如昨日。突然之间,所有的回忆全部崩塌,你意识到“他不在了”,你再也无法听到他说任何一句话,再也无法和他拥有任何共同的经历,甚至,你再也看不见他了。
痛苦、绝望,随之而来。你那么努力地去寻找他还活着的痕迹,或者想把他深深印刻在自己的脑海里,却发现这只是幻想,仅是徒劳,然后希望破灭,心如死灰。
清明,祭祀亡人,表达哀思。哀悼我们的失去,处理、消化因为“失去”而引起的分离、永别和悲伤。当我们真正能够去体验与分离有关的所有感受,走出对“失去”的否认和拒绝时,才可能获得力量,结束这个痛苦的过程,走向新的生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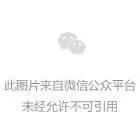
哀悼是一个心理的过程,刚刚经历“失去”的时候,人们常常会否认,不想知道它,拒绝承认它,就好像:我只是做了个噩梦,我只需要醒来,事情就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。然后,大量的情绪喷涌而出,哀伤、痛苦、内疚、愤怒、无力、空虚、孤独……
我们被这些沉重的情绪包围着,淹没着,通过哭泣和哀嚎来表达。接着,是寻找和分离,人们通常会不断地去寻找逝者或失去的东西,并相信自己已经找回了那个人或物,然后又在没有找到它的时候,感到失望、难过。在一遍又一遍地寻找和失望中,开始降低自己的预期,慢慢沉痛地接受这一“失去”。最后,承认现实,接受我们已经“失去”,并把这一“失去”整合到当下和后续的生活中,记得这个人,记得与他所有的经历,并允许这些经历和“失去”进入自己的生活。
痛苦,也会让我们开始沉思,让我们更加深刻、更加强大。当至亲永远离开时,我们内心的一部分也随着他一起离开了。同时,在心灵的最深处,我们又继续保持着和逝去至亲的联系。因为,心中有份爱。
有位朋友,父亲在他幼年时早逝,当我感慨他的“丧失”时,他如是说:“我父亲一直活着我的心中。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,甚至不太记得父亲的模样,但我从母亲、亲戚、邻居那里知道了我父亲是个善良、坚强的人,我一直视他为我的榜样。斯人已去,即便如此,缺席的他仍然对我的生命历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……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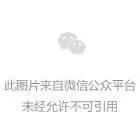
在哀悼中,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与逝者的情感,使得与逝者的关系更为密切,也使得逝者一直存在于我们心中,并在生活中占据一定位置。所以,哀悼,也是一种关系创造的过程,一种与逝者产生新的、爱的关系的过程。
在这个意义上,哀悼其实是对逝者的爱。
清明,哀悼我们的“失去”,珍惜与逝者的同在。